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報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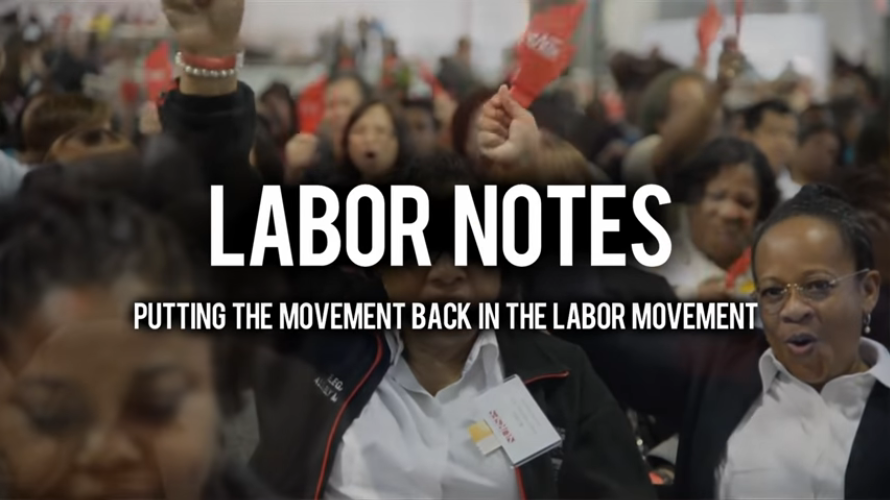
Labor Notes 的重要任務:「把運動放回工人運動裡」,要重新尋回工運的進步性(圖片來源:Labor Notes 介紹影片片頭截圖)。
美國工運組織 Labor Notes 即將在今年(2019)8月16號到18號,在台北福華飯店,舉行一場「亞洲勞工會議(Labor Notes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)」,屆時會有美國及日本、韓國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柬埔寨、印度、孟加拉、泰國…等主要是東亞地區的勞工組織者約150人與會。類似這樣規模的國際工運組織者會議,在台灣非常罕見,而對 Labor Notes 來說,也還是第一次離開美國舉行這樣規模的會議。我想在這邊,作一點粗淺的介紹。
二次戰前的鎮壓
首先,我想從美國的「工運」和「工會」開始。
曾經在全球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美國工運,經歷上個世紀的鎮壓,與國家強力的干預,到今天,基本上是虛弱無力的。最早的總工會「美國勞工聯合會(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,AFL)」成立於1886年,本身有強烈的排外性,在勞動條件上,只看到自己會員工會,而忽視如女性、非白人、邊緣勞動者,更遑論世界工人運動的參與。
到了1905年,AFL受到新興起的總工會「國際工人工會(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,IWW)」的挑戰,IWW 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,號召全體工人階級的團結,以建立全球一個工會(One Big Union)為職志,挑戰以「白種男性典型勞動者」為中心的 AFL,將工運從優勢工人與工會的手中解放出來,訴諸更大範圍的團結,並向資本家掌握的政府發動政治的挑戰。
但 IWW 隨即遭到美國政府的鎮壓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體制,給與國家非常好的藉口,頒布《反顛覆法》、《反煽動法》等,美國政府宣布 IWW 為非法組織,展開白色恐怖的血腥鎮壓,在戰爭中,消滅了 IWW。經歷經濟大蕭條時代,羅斯福「新政」,一方面對工會妥協,承認工會的談判權,一方面透過法規的限制,將工會的活動限制在廠場內的經濟鬥爭。
這一套邏輯,具體體現在被稱為「華格納法案(The Wagner Act)」的「勞工關係法(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,NLRA)」上;基本上它總結了之前半個世紀美國對工運的策略:只要你不造反、不要讓勞資爭議擴大,變成政治問題,我就給工會保障,讓它成為談判主體。
冷戰時期的「立法」與「收編」
兩次大戰期間,1935年,「產業工人聯合會(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,CIO)」從AFL中脫離出來,再開始批判AFL的族裔色彩,成為具進步色彩的新總工會系統,不過隨著進入二次大戰以及接著的冷戰,美國再度陷入麥卡錫主義(McCarthyism)肅清共產勢力的白色恐怖情境裡。
1947年的「勞工關係法(Labor Management Act,即塔虎特・哈雷 Taft-Hartley 法案」、1957年的「勞資關係法(Labor-Management Relations Act,即蘭德姆・葛里芬 Landrum Griffin 法案),除了再次強調勞資爭議必須限於純粹經濟關係,也進一步禁止支援性或政治性的罷工、強調勞資談判的目的必須是「恢復生產秩序」,而國家也可以強力地介入、中止罷工。
 1955年,CIO 回到 AFL ,成為今天的 AFL-CIO ,圖為 AFL-CIO 的標誌,左邊白色的手代表 AFL、右邊有色的手代表 CIO。
1955年,CIO 回到 AFL ,成為今天的 AFL-CIO ,圖為 AFL-CIO 的標誌,左邊白色的手代表 AFL、右邊有色的手代表 CIO。在法律的箝制下,美國進步性工會,以及工人的政治力量受挫,1955年,從 AFL 脫離的 CIO 再度回到 AFL,成為今天的美國「AFL-CIO(勞聯・產聯,或可以理解為美國總工會)」;接下來的故事,就是在這個受到外部限制、同時也高度自我設限的封閉環境下,美國工運怎麼發展了。
時序進入1960年代,面對新的社會運動再起,工會已經不再能在其中發揮領導的作用,從而也使得社運的抗爭,失去了這一股政治的主力,而難以產生翻轉政治的力量。這個時候,美國工會的問題:專注經濟鬥爭、忽視邊緣勞動者的參與,在封閉的系統下,漸漸成為體制的一部分,即便還不至於變成由資方控制的官方工會,但工會的官僚主義瀰漫,已不具有政治上的進步性。
Labor Notes的成立:1979
「Labor Notes 成立於1979年,在美國社會運動高峰的尾期」。
這一次協助 Labor Notes 舉辦亞洲勞工會議的美國「國際勞工權利論壇(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orum,ILRF)」的 Kevin Lin 說到, Labor Note 是由幾個馬克思主義團體的成員共同成立的,但他們不想作左翼的小團體,而希望能夠從事支援進步性組織者的的角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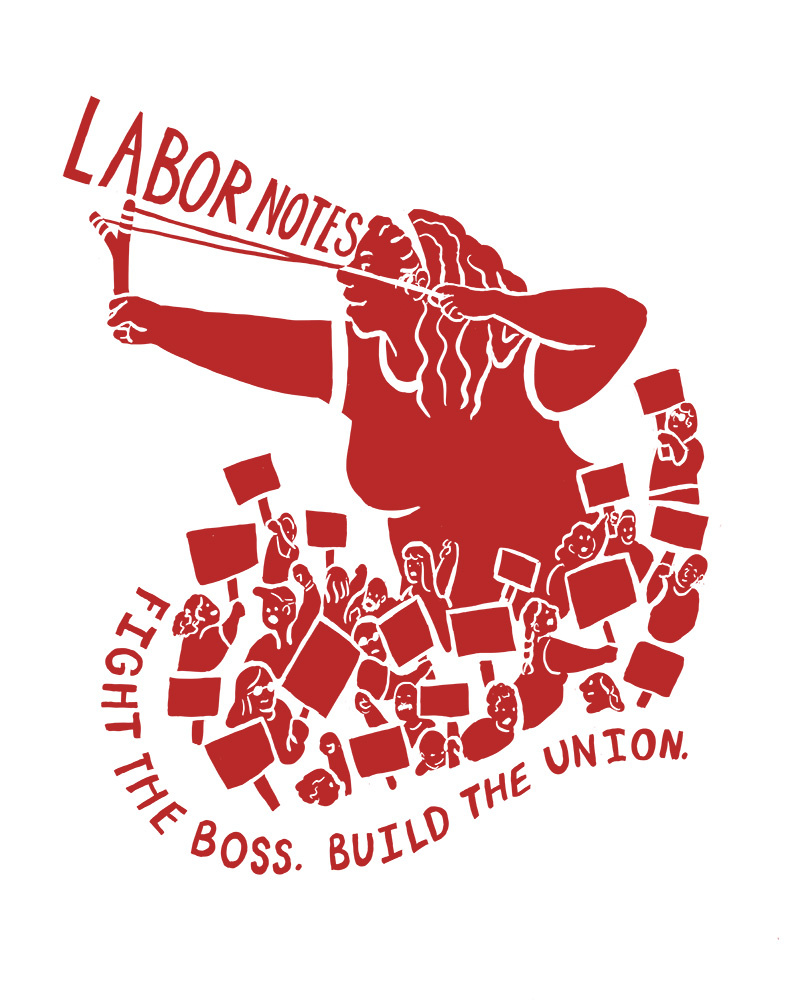
而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,在美國的脈絡下,面對工會的官僚主義、超越族裔的框架、踏出工會所忽視的邊緣勞動者的組織工作,一直是百餘年來美國工運「進步」與「非進步」的一條界線。Labor Notes 成立的宗旨很清楚,是「反對商業化的工會,只是在雇主和工人之間扮演調人,有時甚至偏向資方的利益」。
Labor Notes 表面上主要的工作,是編輯《Labor Notes》這份刊物,把更多的注意力,放到工人的抗爭上,他們希望讓工人自己寫稿,並且發展對工人抗爭的培訓工作,「Labor Notes 對這些工作,並沒有限定是針對哪一個行業或者工種,重點在於組織者的理念,著眼於工人怎麼改變自身…」,Kevin Lin 說。
Labor Notes 本身也不領導抗爭,其主要協助的對象是工人自發的抗爭,組織者自己就是工人,而不是由大工會派下來,由大工會專職人員領導的抗爭,「這牽涉到抗爭的主體性問題」,Kevin Lin 說,大工會往往都希望控制工人的抗爭,這牽涉到「民主」的問題,「在工會裡面,越往上走,越不民主,而 Labor Notes 希望用基層的力量,貫穿工會」。
今年剛好是 Labor Notes 成立的第40年,這40年來,這個「不領導而在外協助」的角色的工作,除了編輯刊物之外,也在美國各地辦培訓課程,稱為「麻煩製造者學校(Troublemaker school)」、編寫「組織者手冊」,並且兩年一度,召集全美各地聯結到的組織者,召開大會;就拿去年(2018)在芝加哥召開的大會,僅僅有6、7名全職人員的 Labor Notes 聚集了來自全美,3,000名的組織者與會。
第一次國際會議,串連的嘗試
或許可以這麼說,一個沒有明確中心的美國主流工會「反對派」已經隱隱成型;那麼在美國之外呢?在國際間已經有一定知名度的 Labor Notes 過去是不是有更多的跨國串聯? Kevin Lin 說,就他的了解,過去 Labor Notes 比較有投入的,大概也就是對於在美國扶持的右翼政權下,遭到鎮壓的拉丁美洲國家工會,歷次組織者的大會,偶有國際的組織者參與,不過絕大多數都是美國本地的組織者,而像這次的「亞洲勞工會議」,還是40年來,破天荒第一次。
那,問題來了,為什麼要這麼做?又為什麼是台灣?
Kevin Lin 的回答,比較是個人式的,過去 Labor Notes 的重要成員 Ellen David Frideman 過去大概15年的時間,在中國活動,並曾經在中國廣州中山大學推動成立勞工中心,也跟日本、韓國的組織者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聯繫關係,至於和東南亞的聯繫,則是也在 ILRF 負責中國項目的 Kein Lin 個人,有一些聯繫,而這一次提出要到亞洲來辦這樣的會議,也就是希望把過去的連結接起來,讓亞洲的工作者能有交流的機會,也影響亞洲工運組織者的理念。
至於台灣,Kevin Lin 說到,一個原因是台灣剛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中間,在地緣上最方便,而歷次國際交流的場合,都沒有看到台灣的組織者參與,其他地方,像是香港,差不多都是類似聚會會選擇的地點,本來國際化的程度高,會議到那裡開,幫助也有限,而就是因為台灣缺乏這樣的機會,所以或許這樣操作,可以提供資源的效果也會更高。
看起來,在會議舉辦地上,也有一點「中心」和「邊陲」的考量。
不過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,既然 Labor Notes 是從對美國工會的官僚主義的批判出發,跟這些他們對脈絡沒那麼熟悉的國家合作,怎麼知道不會串聯到他們最討厭的工會官僚呢?這種人,在亞洲可是一點也不少見啊。 Kevin Lin 承認,這一次是一個嘗試,希望能夠支援到更多國際的工作者,沒有辦法做太多的篩選,希望在過程裡,找到適當的切入點,「上點心,把大家連結起來」。
東亞工運・帝國邊陲
我想,最後在這裡,我也從東亞這個位置上做一點回應好了。前面,花了很長的篇幅,在討論美國工運遭到鎮壓的歷史,以及在這個歷史下,發展出的美國工會的樣貌。而這些,做為美國冷戰前緣的東亞國家,完全是參與其中的;二次戰後,美國對於在其佔領下的日本及韓國,最重要的輸出品,正是美國消滅工人運動過程所淬煉出來的方法。
這一套方法,簡單來說,就是「鎮壓進步工運、扶持保守工會、立法箝制工人運動」,麥克阿瑟的軍政府,將美國的工會法制引入歷經戰爭體制,左翼力量已經被撲滅殆盡的日本,而在韓國,美國軍政府血腥鎮壓工人運動,消滅左翼總工會「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(全評)」,扶持「大韓獨立促成勞動總聯盟(大韓勞總)」,整平場地後,再透過李承晚的魁儡政權立法,嚴格限制工會的任務。

麥克阿瑟(右)血腥鎮壓韓國工運後,扶持李承晚(左)獨裁政權,輸入美國的勞動法系統,並且扶持黃色工會,在韓國複製了美國的經驗。
在台灣,不需要它的美國主子操太多心,1950年代以降,國民黨政權先發動白色恐怖鎮壓,接著自己的黨機器進入國營、大工會系統,一方面扶持為黨國、資本所用的工會,透過工會幹部特權的給予,建立「黃色工會」, 另一方面嚴格立法限制工會的行動,也避免在黃色工會之外,再產生另外的工人運動力量。
在這種情況下,連美國式表面保護工會、實際是限制、規訓工會的法制都不需引入,直到解嚴後20多年的2010年,工會生態漸漸發生改變之後,才喜孜孜地去把麥克阿瑟留給日本的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」當成寶貝,迎了回來。在台灣,當「合法罷工」成為必然的辯護時,工會也已悄悄回到1930、1950年代,在法律外觀下,失去戰鬥性的美國。
結伴同行
工會失去戰鬥性,「官僚化」是在體制裡取得代表權與利益的必然結果,這種現象大概在全世界都有,不過若從美國到東亞的歷史來看,如果有志於工運組織的人,像 Labor Notes 的朋友,是在「找出路」,那其實,大家是迷失在同一個林子裡,當有更多結伴同行的理由。
Labor Notes「亞洲勞工會議」將在8月16到18號,在台北福華飯店進行三天,相關議程將有 Labor Notes 的民主的組織方法的培訓、關注契約工的組織、移工、漁工與家務勞動者的強制勞動…乃至全球經濟下的企業談判、跨國的勞工運動等(詳細議程,還會再更新),現場同步中英文口譯,目前可以接受線上報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