焦點事件記者侯百千報導

在華光社區舊址的一角做著生意,也持續在訴訟和抗爭中的廖金裕。(攝影:侯百千)
大觀社區的抗爭,走到了最後關頭,這些年來,這麼多在都市發展下面對迫遷的人,他們過得怎麼樣?跨過「失去家園」與「抗爭」這些的變數,大觀社區的居民又會面對怎樣的未來?我們走訪了幾位曾經面對這些生命中重大「失去」的華光社區居民,看看「迫遷」對他們的生活,帶來了怎樣的變化?
五口之家一人挑 余秋和:就節儉一點過囉

余秋和一家。(攝影:侯百千)
搬離華光社區後,余秋和一家五口搬到到萬隆巷弄的一間公寓,扣掉租金補貼後,每個月上萬元的房租,對於經濟貧寒的余家來說,是一大重擔;余秋和的話不多,但談到對於現在進行式的大觀社區迫遷案,他以過來人的身份說,政府應該要保障人民的權益,而不是將矛頭指向居民,每個居民可能都有不得已的苦衷,政府應該設法好好了解,並協助安置,而不是直接用法律控告。
過去政府曾向他追討不當得利,金額一度高達3百多萬,當時銀行帳戶還被強制執行,每個月被扣3分之1薪水,僅剩下2萬出頭可以給全家人使用,是後來向法院訴願後才暫緩執行,而官司直到現在還躺在法院,了結之日恐怕是遙遙無期。
自被迫遷後,余秋和獨立支撐一家5口生活所需,每個月不僅需要多負擔房租費,原先周邊鄰里互相照顧的機能也不復存在,面對日漸增加的生活重擔,余秋和淡淡地說:「就節儉一點過囉。」,對於他們一家人來說,迫遷似乎已經是過去的事,是一件已經既定的事實,無須多言,每天所想的,就是怎麼過好每一天的日子。
頭戴著呼吸器的余爺爺,不方便說話,問起他對於政府的感覺,他說他沒有恨,剩下的僅有無奈與失望。
余爺爺1941年出生,今年78歲,他28歲時隻身從彰化北上打拼,以在華光社區一帶的菜市場叫賣起家,1982年,他以賣魚、賣菜所存下的幾十萬積蓄,買下了華光社區的黑瓦房,並自行興建二樓,就此與小他10個月的妻子和兩個兒子,在這裡落地生根。
余秋和的哥哥自小有中度精神障礙,但一家人在華光社區互相扶持,生活還算過得去,直到2007年,余爺爺感染肺結核,而且病情日漸嚴重,不得不帶著呼吸管才能維持器官正常運作,菜市場的生意也沒法做了,全家生計全落在余家次子,也就是余秋和的肩頭上,包括余太太一家5口,每個月依靠著身障補貼,老人年金,以及余秋和一人在物流公司3萬多元的薪水,勉強度日。
而華光社區的迫遷,無疑對當時狀況本來就不佳的余家,再蒙上一層灰,當時余秋和一家奮力抗爭,最後仍不得不在2013年搬離華光社區;現在余爺爺由余太太專職在家照顧,余太太是苗栗人,2000年初她嫁到余家,當時對於華光社區印象相當深刻,她說,當時華光社區鄰里都互相認識,每天家家戶戶互相串門子,坐在木製沙發上談天,景象相當和諧,就算家中有什麼狀況,鄰里間也會互相照顧,甚至連大門都不用鎖;但現在,萬隆這邊的鄰居都不認識幾個,與以前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。
離開傷心地 王昀量:鄰居再見有何用?平添傷心而已

王昀量與妻子重返華光社區。(攝影:侯百千)
過去家還在的時候,這片土地上,有原先日本時期就住在這裡的居民,也有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法務部員工,當時他們在政府的默許下興建房屋,王昀量的父親就屬於後者。
父親隨國民政府來台,在法院當官員的隨扈,也在此興建了20坪大小的黑瓦屋,成為來台成家立業的根基,王昀量從小就在此生活,與各種外省、本省的小孩玩在一起,「小孩也走不遠,半徑一百公尺就是極限了。」王昀量說道,過去唸書、戀愛、工作、結婚生子,人生50多年光陰都在華光社區度過,而面對突如其來的迫遷,他一開始也與政府抗爭、纏訟,但直到2013年,他還是選擇與政府和解、搬離。
「若不和解要賠數百萬,沒想到就算簽了和解也要付數萬元行政費。」,王昀量忿忿不平地說,他簽下和解書,自行花費3萬多塊,把生活50多年的家拆除,之後卻還是被政府「追殺」4萬5千元的「行政測量費」,讓他很是不諒解。
原先他與母親、太太,弟弟和弟婿一家5口生活在華光社區,家人之間雖偶有爭執,但畢竟同住一屋簷下,總能大事化小,小事化無;但社區拆了之後,他與太太一起搬到新店的山區,弟弟與弟婿和母親則是一起住進了南港中繼住宅,而搬離後,王昀量與太太只有在過年的時候,才會和住中繼宅的家人見面,關係大不如前。

王昀量與母親、弟弟與兩個姐妹,過去數十年都在華光社區生活,但這樣景象現在也已不復再。(提供:王昀量)
南港中繼宅是政府當初拆遷華光社區的「安置方案」,但要住進去,必須要有低收入戶或是殘疾證明,兩年一簽,申請條件與一般台北市民無異;至今為止,上百戶華光社區的迫遷居民,僅有5戶入住。
心之所嚮,家之所在,社區被輾平後,家也不復在了,華光社區成為王昀量的傷心地,對他來說是不可扭轉的痛,與從小熟識的居民,也再也沒見面。「見有何用?只是傷心而已。」,社區的脈絡因為迫遷斷裂後,過去鄰居之間的關係也不復再,而從小習慣的社區,「廖家牛肉麵」、「杭州小籠湯包」、「碳烤老麵燒餅」、「盛園燒餅油條」、「金華麵店」、「豆漿店」,王昀量帶我導覽的時候,如數家珍,甚至對每一棵樹的品種他都瞭若如掌,「現在房子都沒了,連剩下的就是這30幾顆樹,也是抗爭爭取來的。」
而談到迫遷,王昀量還是有些咬牙切齒,他對我說,讓他一直無法過關的是背上「釘子戶」污名這件事,華光居民許多都是年紀大且經濟困難的弱勢,卻被政府與媒體塑造成釘子戶,他認為,針對迫遷案,政府應該要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進行調查,並讓住戶參與,以受社會公評,讓弱勢居民洗刷「釘子戶」的污名;另一方面,對於弱勢居民,政府應該要配合社福機關等各單位聯合安置,而非各單位互踢皮球。
對於即將被迫遷的大觀社區居民,王昀量也拋出提問,先有華光,後有大觀,中間數年到底有沒有什麼改變?政府作為有沒有任何進步?這樣才是抗爭的意義所在。華光迫遷案之後,他對於政府可說是已完全失望。
無水無電,攤子還在 廖金裕:我還在抗爭中
直至今日,廖金裕仍在金華街上賣餡餅,有蔥肉有甜餅,鹹甜兼具,用炭火鐵桶古法烹製,價格實惠,路過的雙B轎車駕駛、機車騎士紛紛駐足向他買餡餅,生意看來不錯;他是在華光社區最後僅存的攤商,也可說是最後抗爭戶,華光社區現在已變成一片綠地,在了無人煙的華光社區舊址,他的攤販就在金華街上的一角,持續做著生意,彷彿一切如舊。
社區還在時,廖金裕在金華街上有店面,在抗爭期間他頑強抵抗,還曾跳上雨棚與警察對峙。強拆後,他仍持續與政府進行訴訟,數年來花費不止百萬元,官司直至今日仍未完全了結。他透露,由於他的堅持與一些幸運,讓他取得關鍵的證據,證明他的房產早在日本時期就存在,也大大有利於他的官司,法官甚至在判決書上寫明「政府應給予合理補償與安置」,但時至今日政府仍在互踢皮球,沒有人要提出解決辦法,也沒有人對他有辦法。

華光社區抗爭時,廖金裕曾跳上雨棚和警方對峙。(提供:侯孜餘)
「我現在還在抗爭中。」
廖金裕說,其實他很簡單,就事論事,只要有理他也願意走,但多年訴訟下來政府始終拿不出「理」來,那他也會持續用他的方式抗爭到底。官司雖然順利,但店面早在華光社區迫遷時,也一同被拆除殆盡,但他仍然堅持在原地做生意,無水無電,只能用小LED燈照明,持續生活下去。
這樣的生活也沒那麼單純,他時常被找麻煩,他說,現在天天有黑頭車在附近「站崗」,三不五時來找他「聊天」,希望看看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他這個「麻煩」。但廖金裕說,他就算是再繼續被騷擾,還是會持續抗爭下去,不會屈服。
仍在原地做生意的他,不時會有過去華光社區的居民回來與他買餡餅,甚至有幾位華光居民,直接成為他攤販的「幫手」,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抗爭,而直至今日他與政府還在繼續纏訟中,官司還在打,這也代表華光居民廖金裕的抗爭路,還會持續走下去。

廖金裕:「我還在抗爭」。(攝影:侯百千)
同樣的故事,一直來,一直來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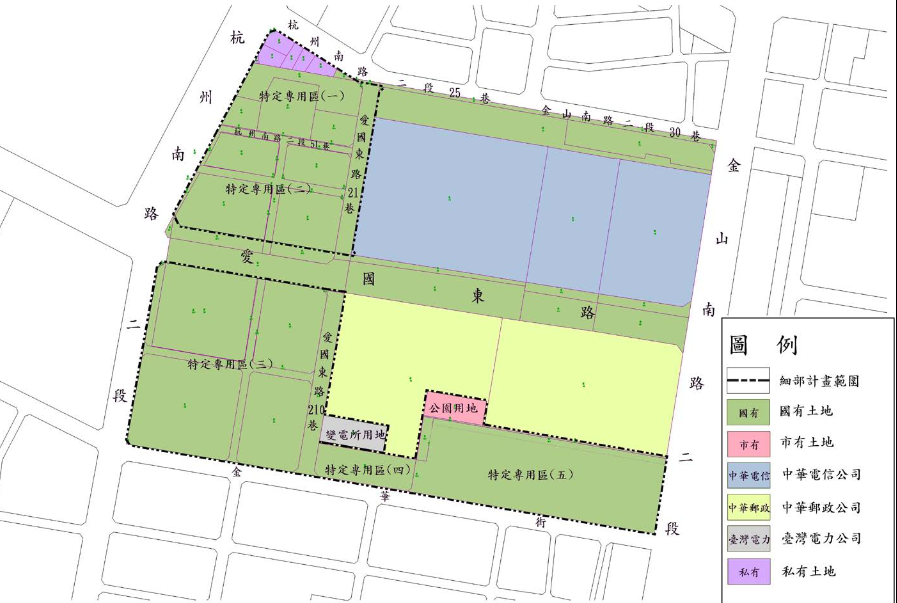
各種虛華想像一一落空,6年來華光居民的家沒了,這塊地卻一直不知道要幹什麼,今年因為東門、南門市場拆遷,攤商們將移到華光社區原址,好不容易為這塊金磚地找到了一個用途。〈空許繁華不堪回首 華光強拆後六年 南門市場將遷入〉
剛剛經過幾天陰雨的浸潤,地上的草又長了些,2007年,「金磚計劃」下的「台北華爾街」比雨後的彩虹消失得更快,2012年,又來了「台北六本木」計劃,沒多久也跟著成空,在這片被形容為「金磚」的土地上,對於有權力的人來說,好像隨便哪一種紙醉金迷的空中樓閣,都比「家」來得更酷炫、有價值。
6年了,今年(2019)稍晚,這片該長卻沒長出榮華富貴的青草地上,才將迎來新一批的暫住者:同樣在都市計畫中,未必情願搬遷過來的東門、南門市場攤商;而失去了「家」的人,日子過得更難了,不過生命總是頑強的,怪手推土機壓彎了人們的腰桿,但還壓不斷他們的呼吸和心跳。萬般無奈者,同樣的故事,一直來,一直來。
沒有了家的人,你們好嗎?